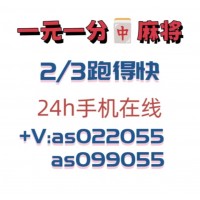诚信可免押进亲友圈验亲友圈
/> 冬天的山,是最耐得住寂寞的
褪了红,清了绿,瘦骨嶙峋的,象是清水洗过一样,还了本来的模样
枯了的枝叶,还僵硬在树杈窝里,一动一动颤颤着,想把满身的寒气洒洒抖落
村庄黝黑黑空旷旷的,和晒暖阳的老汉一样,眯着疲惫的眼
“叭嗒”“叭嗒”里,缕缕旱烟寥寥飘起,有一搭没一搭的,好像头上的太阳,虚虚的,嫩嫩的,绵绵的
偶尔,也有弱弱的风会从挂着的柳条上滑过,悄悄的,暖暖的,象是农人棉袄里冒出的热气
一切都那么静谧,安宁,懒慵
山窝中的柴门里,一阵没一阵地有小孩的哭声溢出来,惊诧了打鸣的鸡
北风一吹,柴门推开,狗吠声,追打声,哭叫声混成了一片
这中间,夹杂有一声弱弱的老腔,“来生妈,来生妈……”倏忽间,随着一声呵欠,一切又归于平静,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于是,女人们溜下了炕,抱一把柴,就有炊烟直直地从山洼里飘过
初冬的夜晚,没雪,只有干干的潮气,低徊着,漂移着,浓浓的,扯不断的棉絮一样,裹得山坳空空的,紧紧的喘不开气
月亮是后半夜爬上来的,半张着嘴,咧咧的,清清的,照得柴门下台阶的影子,长长的,像一条瘦瘦的竹竿,搅得梦也是碎碎的
有哭声啜啜地,轻轻地,沟水一样孱弱地流淌开来,夜漂了粉一样“哗”就白了
睡梦轻的老人翻身坐起来,收起发麻的腿,长叹一声,“哭山的又来了
来生妈,遭孽啊!” 老婆子的来生妈已经70多岁了,牙口还好
眼睛本来好好的,硬是让眼水水给哭浊了,看不清对面的人
但她看得清对面的山
一进到冬天,她就对着一个方向哭,哭自家的后人来生
来生本是个安安份份的庄农人,长粗茶淡饭过了40多年,就知道吆着羊去对面山坡上吃草
冬去春来,看着温润的羊群变白变胖,心里的自在就像那长起来的春草一样,放个皇帝都不当
可他不甘心,经不住别人的劝,非要跟人到南方浪世事去
走的时候,给他妈磕了三个响头,说年底就回来了
年底了,别的人欠着工钱回来了,他却等着要拿自己的钱
结果钱没要上,被人乱棍打死了
过完年,邮局捎来了一沓子新飘子,还有一张来生站在铁路边的照片
庄里的年轻人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来生这样张狂的样子,不知道咋日弄的呢
来生妈拿着照片,拿着钱,一家一家问,一户一户找,说你们来了,来生咋不闪面呢
从崖头到崖下,从白天到夜里,不吃不喝,眼哭肿了,腿走跛了
庄里人看她可怜,就说你到对面山上去喊吧,七七四十九天后,来生就回来了
就这样,每到夜深人静时,来生妈的就对着山坳哭,喊,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尖
“来生,我的娃,你死到哪去了……” 来生没了,女人改嫁了,羊就没人放了
留下一个孙子,鼻塌嘴歪的,整天就晓得往外跑
她盼着孙子能守住这个家,可孙子不喜欢放羊,嫌有臊味;也不喜欢她,嫌脚臭口臭
他只喜欢去镇上看录像,喝酒,来回几十里山路,不嫌累
录像看腻了,就呆呆地杵在柴门前,痴痴地瞅对面的山,一个一个的数山腰腰里的窟窿
直到有一天,他对着空山说,我会找回爸爸的
但来生妈却不信,她担心孙子也会和儿子一样,飞走了,再也不回来
仲夏的夜里,月光幽幽的,照在墙角的一口棺材上,那时来生妈将来要去的地方
儿子死了,她还活着
一月一日的,上面落满了厚厚的尘土,她不让孙子打扫,说要不然来生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让孙子把再没刷漆的棺材移到门口正对上柴门,等夜深人静时爬在上面,拍打着,用哭喊声来打发后半夜的光阴
冬走了,春来了,山绿了,来生妈的哭声已经变成了娃娃们的催眠曲了
这时的孙子,酒也喝够了,喉结也长粗了
终于有一天,他和棺材里的钱一起消失了
庄里人议论说,又少了一个山里人,来生妈的罪孽更深了
这一夜,他们惯常在等待那一声悲切绝望的哭喊,可是柴门里面静静的
早上天一放亮,他们发现柴门的门框上悬了一面明明的镜子,他们知道,那是禳斩邪气用的
月光亮亮的,白白的
对面的山坳还是那么瘦骨嶙峋的,不过它们很快又会染绿染红,像姑娘们的头发,蓬蓬松松臃臃肿肿的,在葱郁之外倒将要缺少一股清香之气
来生妈没有等到孙子回来就自己睡到棺材里,再也不想爬起来
等庄里人发现时,身上已经淌蛆了
她的坟就在对面山坳里的一个窟窿眼底下
-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
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有一年,秧苗给烧了
了 我们经常肚疼
我们将腹部称为肚了
肚子疼了,我们便跑回家,趴在炕沿上将肚子轻轻地硌
一会儿,待硌好了,便再和娃子们去疯去耍,或者提着荆篮儿到坡里去挖野菜
那些漫山遍野,开着或白或蓝小花的苦菜、曲曲菜,七根菜,秃头妮子菜,绿格生生的,可都是我们伺候肚子的好饭食
当然,也有在炕沿硌不好的时候
我们便只好去告诉母亲
我们说:“娘,人家肚疼
母亲正在灶间烟熏火燎地烀一锅猪食,母亲头都不抬:“你到炕沿上去趴一会儿
”我们一脸的苦丧:“趴哩,没价趴好
”母亲便说:“早不死的王八羔子
”母亲丝毫不察觉她这是在骂自己,一下撸掉头上的冒头布子,一边抽打衣上的黑灰,发丝里萦绕着袅袅的饮烟从灶屋走了出来
娘立在门口,一下吸足了力气:扬着嗓门儿喊: “秃子他爹哎——,你快回来看看哦,秃子又肚子疼了哎——” 父亲是在南边绿郁郁的大山上劳动着的,他和队长及社员们一走起,说不定是剜谷苗,还是在给冒了头的绿杆子高粱喂猪肥
娘的喊声,山听到了,山里的野雀子和老鹰也听到了,爹便听到了
“听着哩——”雾嘟嘟的山里一个粗犷的声音远远地传回来
我现在清楚地记得父亲回家的情景,父亲的脸上油着白光光的汗,进门将锄头在门墙上一杵,就直奔院中的水缸去
父亲一手拿起葫芦水瓢,一手揭起秫秸的锅盖,头一扬,就将多半瓢清水咕咕倒进肚子里
然后用手抹一把溅到脖子外面的水,一边甩着卟卟的步子迈向屋里: “疼得怪厉害吗?” 时隔多年,我一直以为是那些看不见的虫子给了我们亲切的父爱
父亲的手掌多么地宽大呀
父亲令我们在床上仰身八乍躺下来,用手一下撩开我们小小的衣裳,让我们露出有一些白,但漆满了黑灰的小肚皮
我们的小肚皮没有了平日的圆润与光滑,突然在什么地方冒出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硬疙瘩
于是,父亲一边将一只手放在上面,一边自语着:“娘的,又有一个蛋疙瘩呢,又该给你们药虫子啦
” 父亲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将那宽大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肚皮上轻轻揉动起来
肚子开始还在疼,甚至显得更疼了些,但在父亲的轻轻揉动下,那块疙瘩便像一块石头渐渐地化作了一团泥,一下软和起来
我们的小腹一会儿便变成了一只小小的水袋,肚疼便彻底消失了
我记忆犹新的肚疼是上小学二年级的事情
有一天放学回家,吃一块娘早上烙下的玉米小饼,肚子便猝不及防剧痛起来
我一边叫着,一边在床上打滚,脸上的汗和泪到处都是
我的肚子里面似乎有一团火,又似乎有一把刀子在到处乱戳
我疼坏了,就折起身,双手抱住肚子,将身体弓一样弯着,把要命的肚子用力向上举;这样还是疼,便又将双脚高高举到墙上,将多半个身体贴在墙上挣扎
我没命地喊着娘,娘满脸惶惑,手足无措地站在炕前,我想起了爹那宽厚的巴掌,于是又去喊爹,我就在这样的期望中看到了绝望,后来疼昏了过去
后来,我醒了,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父亲一双柔慈的目光,——我是在父亲一双大巴掌的揉动下才醒过来的
父亲说:“是该给仨儿吃药药虫子啦
”我看到父亲的脸上竟浸满了泪花
当初父亲口中说的虫子,我们并不知道它就叫蛔虫,尽管他与我们的生死有很大关系,但我们却不能也极少去探究它
那时,我们三五个娃子在山里割兔草,拾柴火,剜野菜,一起用手扒出只有山羊角大的地瓜用烧了吃,一起站着撒尿,或蹲着大便,那些长长白白的虫子便随着弯曲的粪便排下来,它们麦杆一样粗细,竹筷一样长短,两端尖翘,能够排下来的,大多是不小心走错了地方,或者已经死掉的
活着的总要挣扎一番,从粪便中艰难地爬出来,在地上蚯蚓一样扭动
我们用手摸起石块,气愤地喊:“砸屎虫子
” 我们便是在砸屎虫子中长大的一代
砸屎虫子的经历,令已然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我们自愧和内疚
但自从一个名字叫做王朔的作家将高尚的北京人“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的口头禅热传之后,我便稍稍有一点自信地抬起了低垂的头颅:人家有知识的人就是幽默,竟可以将过去把我们置于死地的蛔虫比喻地那样俊巧可爱,——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无所不知,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无所不在
这们,平素里就喜欢著一些小文的我又有什么可以内疚的呢? 蛔虫的确布满了我们的身体
疯玩了一天的我们夜里忽然醒了,被作业(作业并
咬住牙,让腿脚做着板滞进取的提高,哔竟达到天都峰下的颔
时于今日,当我轻轻敲击下这一段段略显惨白的笔墨时,早已跟着南归的列车,重又回归到本人平常的生存中,离开了乌海朝夕八点中的阳光,离开了黑烟滔滔的大烟囱,离开了房主年老叔家不到天明便咯咯呼唤的鸽子,离开了戈壁中捂不住的流沙,草地上看不尽的牛羊,一米阳光的烧烤,街边迷人的串串,拐弯早餐店的土豆包回到拥堵的食堂,凉爽的校舍,温暖的班级
以上就是关于信誉保障上下分模式红中麻将跑得快群棉袜全部的内容,关注我们,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VIP第1年] 指数:1
[VIP第1年] 指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