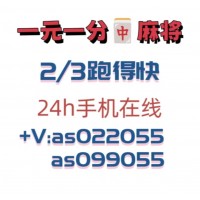以前,我去母亲那里是即兴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因为母亲的上学,我却不能来去自由了
每次去,必须先打过去一个电话和她“预约”
父亲去世后,我便成了母亲木纳的女儿,了无生趣的语言,生活里也很少有向母亲撒娇过,更不用说在电话里了,除了千篇一律的问安,永远都是波澜不兴的平和
而母亲总是接过电话,关心我的工作或生活
和父亲一样,母亲最希望听到的,是我在哪方面有了些成绩,日子过的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
我开始咀嚼这些话,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真理
于是我一边回应着:
就这样,我每天在学校里住,到大军家吃(常常也跟大军在一张床上滚)
当时,马大妈常说阿大每天都要背一两百斤重一袋的麻包上下车,工作苦,而几个孩子都在学知识长身体的年纪,就是一分钱不存,也要尽力把伙食办好
于是,饭量大得惊人的我,每天都会与一家人围坐一桌,痛痛快快地吃马大妈做的鲜美可口的菜饭
可我每天所能做的,就是在饭后帮着大妈收拾一下饭桌,扫扫地,或到井里拎两桶水
总之,我那时的心情是复杂而愧疚的,好在二老都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女,没有丝毫的责备或偏心
那次我们班里要交什么钱,我已记不起来了,反正数目不小,大妈便逗大军我俩说钱只够交一个人的
大军就急了:“你说话不算话,你说过要帮助人家的
”大妈笑笑说:“难道我说过不帮了吗?”有的周末,我们也会帮着大妈侍弄侍弄仅有的两小块菜地,那样的日子我感到幸福而开心
有一次,我和大军兄弟俩还在地边照了一张像,如今,我还完整地保存着这张只有两寸的黑白照片
每次翻看,总会浮想联翩,温馨荡漾
第一节课下课,他们还在聊着,我说过丽是一个高明的侃客,而飞也是一精明的幽默家与评论家,还带着几许天真的童性和丽聊
其实有时我觉得丽比飞还有单纯一些,但是总是想到她和太多男生的聊天记录与场景,弄得我从不敢认可她的单纯
为了避免尴尬,我唯有写写日记
飞当然叫我转过身去一起聊,我没有表情的说不用了,我还要写日记,我听到丽的一声嘘声,感到了内心蹦出的一丝委屈
四周的沙坨开始迷朦了,如一幅淡而薄的纱帛披在上面,使这黄昏更加神秘
大海的喧嚣声隔着沙坨传来,恒久而遥远,好似在暗示着一个亿万年的神谕
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双手分开野苇草,双脚试探着向深处走去,便有苇叶热烈而羞涩地拥抱着我,而脚下分明感到水与沙发出的细微而愉悦的欢呼
如果是在白日的沙滩,我会郁郁回首,凝望身后那一行或深或浅的脚印,而此刻当刹那的感觉产生时,便立刻被另一种情绪化解了
自然的真诚融化为野苇草亲切的实在,它们纤细而挺拔,默默而伟大,它们以每一个优美的姿态接近着我这样一个疲惫的人,并捧出全部的热情为我抚去心灵的污垢
是的,我没有必要去回顾什么,没有必要去祈望什么,我所应该有的只能是敞开思想去承受去感恩,并在心底托举出真情的歌唱
以上就是关于生活更精彩跑得快。红中麻将上下分群说然全部的内容,关注我们,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VIP第1年] 指数:1
[VIP第1年] 指数:1